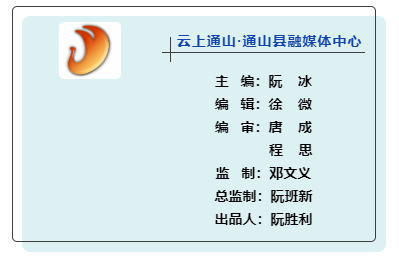娘,我永远忘不了二十年前的今天——2000年3月26日。
那天,天阴沉沉的,还下着冷雨。您的病房里亮着灯,生着火。来探望您的亲友都坐在病房里陪着您。


晚饭后,近一天来未曾开言的您,突然用低微的声音叫我,我快步走到您的床前。掀开帐门,只见透过老夏布蚊帐发黄的灯光照在床上。您平躺着,瘦骨如柴,脸色像土一样黄,紧皱眉头,露出非常痛苦的神态。
一个月前,由于胃癌细胞扩散,您常常痛得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却从不喊一句,也不叫一声。实在受不了时,您才轻轻地呻吟一两声。
娘啊!我知道您是怕吵到我们,又怕我们听了心里难受。
娘啊!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如果我能替您痛,替您难受,那该多好呀!
您听到走近的脚步声,知道我来到您的身边,艰难地睁开了眼睛,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我....不行了,我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哥。你弟在北京做生意,不便管你哥。你虽身体差,但要尽力要照看好你哥!”妹妹听了,忍不住低声哭了起来,我一手拉着妹妹 一手拉着刚进来傻笑的哥,一齐跪在你床前的踏凳上。面对着病重的您,面对您期盼的目光,我心如刀割,啜不成声:“娘....娘.....您放心,我.....我...一定会管哥哥的。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决不会饿着哥哥,只要我有穿的,决不会冻着哥哥”。
听完我的话,您老看了看我们互相搀扶的兄妹三人,安详地合上了双眼,任在场的亲友怎么呼,怎么喊,您都不应。舅妈对我说:“你娘累了,撒手离开家人到天上享福去了。”
当时,我泪如泉涌。想起您为养大三儿一女,受尽了罪,吃尽苦。先后两次做屋,不知饿了多少肚,流了多少汗。
我记得,每年春夏两季,您带我和哥哥到山上扯苦菜,每年都晒几箩干苦菜。每年到挖薯后,红薯就是主粮。每餐闷一炉罐薯,再熬一茶罐粥。粥被我们兄妹四个和父亲全分了,您从未吃过一口。
您不光从生活上关心我们兄妹四人,更用自己的行为教育着我们。我记得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有一年快过年了,你没给我们买一点糖果,却称了一小菜篮盐,叫父亲沿家送给队里最困难的人。
七十年代初,您任生产队妇女队长, 您事事带头苦干。特别是农忙时节,您带着女社员们出早工,开夜战,根本不顾家。害得我既要带妹妹,又要做饭、送饭,还要养猪。记得我读初一时的有一天,上午第二节课快下课时我才报到进教室。至今同学聚会时,有人还当笑料笑话我。
娘,您既是我们做子女的榜样,也是一大家侄儿、侄孙的楷模。不管谁家做事,您总是第一个到,做事尽心尽力。家中不管谁做错了事,您都会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教育。使大家既爱您也怕您。
娘,大公无私是您老的品格, 勤耕苦做更是您老的秉性。在您得病的那年秋天,您还在甘垅割谷,面前坪捡山茶,大角山挖薯。有人问您,这大年纪还这样做,为什么?您老回答说,我有崽,有老孙。


娘啊!您老了还时时想的是家庭,想的是儿孙,却从来没想过自己 。病前,您没有自在休息一天;您得病,也没及时的发现;病后,也无法进行治疗(一检查就是胃癌晚期)。想到此,怎不叫我肝肠寸断,悲痛万分。
娘,您走后,哥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病发作时,父亲便叫我帮他给哥喂药。
2003年6月,父亲因病去世。弟跟我商量,准备带哥哥到北京去。我说:“弟,你在北京是做生意,带个精神病人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我在家乡工作,早、晚能照顾哥。病发我可请假。”弟便同意哥留在家里,由我照看。
开始,我用您管哥哥的方法照顾哥哥。当他发病时,不知怎的,给他喂药一点作用也没有,吃药跟冇吃药一样(可能是长期服药,体内耐药了)。没办法 ,我只得由着他,看着他,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乱跑,不打人,就不阻止他。等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一日三餐,我夫妻一起送饭(以防不测)。每次发几天病后,他就会慢慢清醒。我夫妻俩就把柴、米、油、盐、菜送给他,教他自己煮饭吃。不发病时,他的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
为防哥发病时乱跑,伤人伤物。我便将家门前围上栅栏,只留一扇门出入,让他在老屋和大菜园自由活动。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到县学习半个月。结束后回家一看,不得了,哥把菜园的庄稼毁了不算,还把土搬到老屋檐沟。高的地方到了窗户 ,远看就是一个长长的土坡。我没日没夜的整整干了一星期,才将土全部搬走。幸好那段时间没下大雨,否则一连五的土巴房就泡汤了。
哥还爱上屋顶翻瓦,弄得房内大雨大漏,小雨小漏。五年前,我和弟弟给他做了一间水泥平顶房,用上了电炒锅、电饭煲。去年,政府还给了哥低保。
娘,现在哥的病已经轻多了,您老就安息吧!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哥哥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