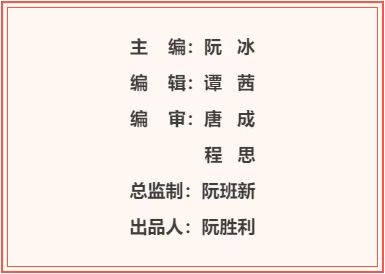碧草湮烟尘
作者:谢晓文
这里,分明是一片废墟!
沙尘飞扬,一路行来的蓝天被浸染成了灰白色。前方天地俨然混沌未开,白茫茫一片。六月初的阳光,不乏热烈狂放,肆无忌惮地横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躺在残缺的土夯围墙上,晃白晃白的,刺得眼生疼。左急转弯,上坡公路那边的高山像是要迎面撞过来,山下的碎石机正“哐当哐当”地响着,像歇斯底里的疯婆娘。
我们转弯,没有上坡,在碎石机斜对面,在围墙终端,停了车。下车步行,折转进围墙,入眼便是铺天盖地的碧绿,丛生的杂草肆意蔓延着,分不清哪是后背山坡,哪是平地。不远处,两三排红色的砖瓦旧房努力地点染着,孤伶伶地静默着。近处的草丛中,隐约可见散落的农具,锈迹斑斑的,不知是犁耙、锄头还是铁锹铁锨。不见人影,每一处都在张扬这里的沉寂和荒凉,只有初夏赋予的草的青绿,让人感觉这是块活着的地方。
所以,我猜测,这里,决不是陈大姐要寻找的故地!
然而,倔强地挺着后背的的陈大姐,却果断地踏上了草丛中的小路,蹒跚向前,张望着,辨认着……
皮肤白皙的陈大姐其实七十多岁了,满头银发,腹部肌肉在岁月的拉扯下,松弛垂垮最厉害,但精神矍铄。年龄小她近三十岁的姐姐却说,她心态年轻,叫她大姐更合适,于是随行的我们都叫她大姐。
陈大姐是开国少将陈沂之女,邮票设计大师。这次不辞辛苦,不顾舟车劳顿,在我姐的陪同下,专程从北京出发,落脚通山,经富水,至阳新,一路颠簸,只为重返她“文革”初期下放的五七干校看看。
我们紧跟在陈大姐后面,在与围墙平行的小径上步行约三百米时右转,面向山坡。用脚拨开杂草,觅得一条小路,向砖瓦红房走去。突然,陈大姐声音颤抖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我在这里呆过了四年时光!”她加快了脚步,朝一幢竖列的砖瓦红房走去。
我讶然,如此僻远荒凉之所,会是当年那个几千人聚集生活之处?会是那个热火朝天的劳动改造之地?那么,那砖瓦红房后面的山,便是半壁山?碎石机碎的,是半璧山的岩石?我来不及梳理清楚,陈大姐就在这幢房子前,觅得一小块未被杂草侵占的空地站定了。
我靠近她站着,试图看清她墨镜遮掩下的心绪。然而,她又起步往残破的木门前走去,用手摇了摇生了锈的锁,见没动静,便往房子左侧走去,踮起脚尖,朝房子左前方的大窗户望去。窗户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缺口,没木框,不知哪年蒙上的油纸已经变黄,垮吊了一半,软软地垂挂着,酷似古人丧事场面垂挂着的白色帷幕。朝这个缺口望里面,空空如也。陈大姐却激动地说:“我原来就住在这房里。这里所有的房——”她瘦小的手往左侧那边的房一一指去,“都是我们自己建的。我们自己烧砖烧瓦盖着住,自己种粮食种菜吃。我们筑堤造田,拓垦荒原,造了许多田地。我还见人上过吊,抬过死尸。当时受的苦,常人感受不到啊,后来回想起来,就像一场噩梦。不过,这也是我成长中的一种特殊历练。在历练中,我变得坚强能干起来了。”说到中途,她声音低沉了下去,到最后,却透露出明显的自豪。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一个荒唐扭曲的年代!兴奋与悲苦并存,邪恶和信仰共生!我同情而又崇敬地看着她,看着她的面颊在阳光下微微泛红,她的银发在风中熠熠闪光。
“到那边去看看吧。”良久,她折转往右,领着我们来到两排长长的砖瓦红房中间。此处杂草较少,有几棵高大的树木。树木枝叶繁茂,阳光从树叶间筛落下来,在陈大姐身上摇曳出炫目的花斑。依然没看见人,我们尝试着大声问:“有人吗?”无人应答,一片寂静,鸟雀都销声匿迹。
在两排房中间,继续向前,走到尽头,迈下去,上几个青石块砌的小台阶,就到了对面的两排房中间。第二排房的第一间房外墙壁上,挂着一把棕织扫帚和两条抹布。应该有人居住,我们惊喜地跨上走廊。门大开着,随着我们的大声问询,一个拄着木棍,头发稀疏银白,身着黑底淡黄叶片唐上装的老大娘,颤颤巍巍地走出来。她脸色腊黄,前倾着身子。我们反复三四次,大声说明来意,她才听清楚。听清楚后的她似乎很激动,紧紧握着陈大姐的手,边摇边说:“回来看看哈?好,好,回来看看好!”
她叫我们进房坐。我们往房门口瞧进去: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进门左边的角落,是生火的炉灶,炉灶上摆放着锅碗瓢盆,正对着门的窗户左侧摆放着一张单人床。整间房只一把椅,一个小凳子,我们想进去坐着喝口水的念头都熄灭了,便都折返站在走廊。
陈大姐连声叹息“可怜啊可怜”,凑近她热情地问这问那。但老大娘耳朵不好使,偶尔听清了两三句问话,回答的口音却让人难听懂。我依稀听懂了“都走了啊”“不回来啦”“我留在这,不走了呢”这几句,不知是指她的子女走了呢,还是指当年下放到这里的所有人。陈大姐倒是像遇到了下放时的故人,似乎能听懂她的话,聊得甚是投机。两人聊着聊着,竟亲热到勾肩搭背的程度了,最后,还让我们给她俩拍合影留念。
和老大娘告别后,陈大姐仍频频回首,频频挥手。我也跟着频频回首。回首眼眸中,红房子前的老大娘呆呆伫立的,佝偻着腰,如一张经历了千年沧桑的弯弓,苍老而孤独。她一直挥着手,直至在我的目之所及处,红房成一条线,她成线上的一个点……
“她是本地人,还是当年下放到这里,后来一直没走的人啊?”我问陈大姐。陈大姐沉默不语,仿佛陷入了沉思,表情凝重而悲怆。我不敢再问,随着大家出了围墙,来到围墙外的马路边。
陈大姐回过神来,抬头望着路下辽阔的田野告诉我们,这些田地就是他们下放时造出来的。他们在这里干活,诚恳地劳动改造,有过兴奋激动,有过委屈悲泣,有过迷茫困惑,有过欢乐收获。我扫视着这一大片田地,仿佛看到几百号人在弯腰躬背,紧张有序地传秧插秧;仿佛听到“嘿呦嘿呦”的吆喝声和“加油!加油”“你来吟诵一首”之类的叫嚷声;仿佛闻到从握镰刀的手中与踩打谷机的脚中流窜出的稻谷香……
眼下,田野在亮闪闪的水洼中泛滥着杂乱无序的绿意,葱茏而疯狂,叫人辨不清是庄稼还是杂草。凭借颜色的深浅,依稀可分辨几丘田——田埂也许有意退隐在青草中,让每一丘田泯灭个性的张扬,融合成一个大集体。空旷无人,鸟儿也懒得飞掠,只有寂静,一如永无止境的暗夜。
“荒了啊!”陈大姐久久凝望着,轻轻叹一口气,像风中飘过的柳絮。
之后,我们去了邮电部五七干校纪念馆。小小的纪念馆,像燃烧的火堂,墙壁上贴满了红色的图片和文字说明。每一张图片都触目惊心,像跳动的火焰,烧灼着你,又像涌动的浪潮,荡涤着你,把你生生拽进那个或激情澎湃或提心吊胆或悲喜交加的火红岁月。这些图片中,有肩挑担子,笑得开心灿烂,皮肤晒得通红的健壮劳动者;有三五成群,扛着锄头,昂首挺胸,手臂后扬,踏步向前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云集红旗下,高举小红本,喜笑颜开,张嘴高呼的聚会群众;有几幅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大型红色邮票……而少量用照相机拍下的黑白照,则真实展示了当年在此地的生活、劳动、学习、娱乐乃至批斗的情景。
我的兴趣更多的在文字简介里。我逐字逐句阅览,五七干校的缘起、发展、规模、停办等情况以及下放者的部分姓名一一呈现在眼前,我之前模糊的认识得以清晰化。我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唏嘘,为下放到这里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恶劣的环境中,在繁重艰苦的劳动中,甚至在莫名其妙的批斗中始终坚守信念,相信党和国家,保持昂扬乐观的精神而赞叹!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唏嘘感叹中,这首歌仿佛从渺远的天际飘过来,在我脑海中久久回荡着。
从纪念馆出来,清新的空气扑鼻而入,我吐一口气,沉重的压抑感一扫而光。抬眸望去,阳光明媚,天空湛蓝,青山依旧,芳草碧连天。繁华盛世,历史的天空被洗得澄澈明净。在今人的抚今追昔中,在后人的反思修正中,每段历史都有其存在的必然和意义。
离开时,车缓缓前行,陈大姐头伸出窗外,默默回望着。那砖瓦红房,那在田野中延伸至天际的碧草,终是在路上扬起的尘土中模糊了,在回眸中逝去了……
我的耳畔,飘起了若有若无的歌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这一别,四十年前,于陈大姐而言,转身已是一个清明盛世;今一别,碧草连天,湮没如烟往事,永生不复再见。
这一天,是2021年6月8日!我人生中体验最独特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