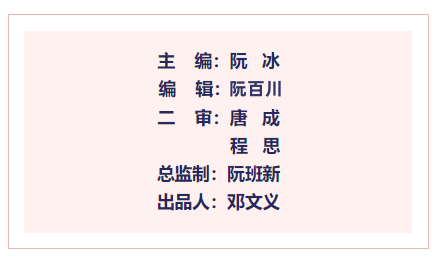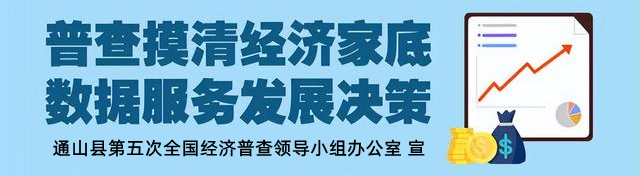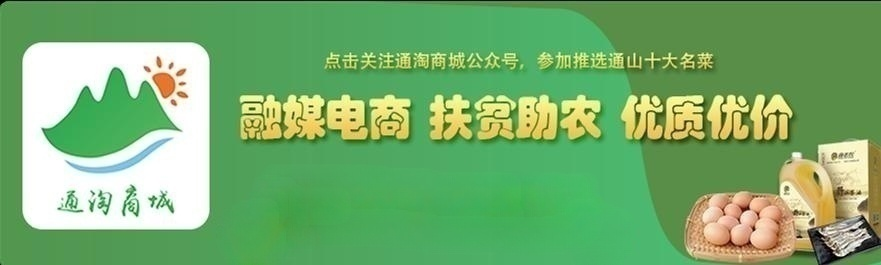母亲的菜园
作者:阮长兴
每次回家,总要去母亲的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母亲也总是从菜园里为我采摘大包小包的当季菜带回城里。
母亲今年72岁了,按说到了这个年龄,本应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但母亲由于几十年间养成的劳作习惯,闲不住,在城里住不了几天,就吵着,非要我送她回老家住。如她所说,在城里干坐着,浑身不舒服,还会闲出病来。我曾经叫姐姐和妹妹劝过母亲不要再干活了,可是她们的劝语也似乎不起多大作用。于是,在老家的日子里,母亲因有太多空闲的时间,兴园种菜便被顺理成章的纳入到了她可控范围内,给了她闲不住的理由和忙碌。
母亲的菜园在老家屋后背的山坡上,大约有100米远,呈半圆形,计六分地,原先是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坟地,六几年为响应国家号召,爷爷把曾祖父母的坟墓迁到别处改成了耕地。七几年田地到户后,生产队顺理成章的把这块地分给了我家。由于离屋近,母亲就把它种成了菜园。
在我的记忆中,菜园倾注着母亲的心血,母亲把菜园里的菜苗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平日一有空闲就往菜园跑,松土,锄草,除虫,浇水,施肥,母亲守望在菜园里,抛洒着汗水,辛勤而快乐地耕种着,一脸幸福地盼望着沉甸甸的收获!春冬,母亲在菜园里种白菜萝卜和葱蒜,夏秋就种茄子黄瓜和辣椒,瓜瓜果果发芽开花抽穗,一地生机勃勃。一年四季,菜园没有闲着,母亲也不会闲着。她一下剥回来一抱菜叶,一下摘来几个黄瓜。那鲜嫩水灵的黄瓜,冲洗干净,嚼在嘴里脆脆爽爽,满口清香。在那缺吃少喝的年代,母亲种出来的蔬果,不但养活了我们一家十口人,让我们的餐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让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来。
母亲说:种菜是一项细致活儿,虽然辛苦,但能带来无限乐趣。“种菜如绣花”、“一亩园十亩田”,施肥、松土、整畦、下种,是要花费母亲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这个时候母亲连蔬菜的影子都看不到,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希望却能给母亲带来很大的鼓舞。因为母亲相信,用诚实的种子种在水肥充足的土壤里,人勤地不会懒,出一分劳力就一定能有一分收成。
小时候,我常去菜园看母亲种菜,她先整好地,再用锄尖拔拉开一道道浅沟,然后把仔种撒进去,最后用锄头推动沿土将沟埋住。等过十天八天,那平整湿润的菜畦就会冒出又绿又嫩又茁壮的瓜菜的新芽来,这时母亲也会露出最灿烂的笑容来。
母亲常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母亲给菜苗浇粪水时,不是鸟儿啼鸣的清晨,就是倦鸟归巢的落日黄昏。母亲说这个时候浇粪水,便于菜苗吸收养分。而且浇洒粪水时,一定要浇在根脚,要是浇在菜叶上,菜苗就会慢慢枯死。等到菜苗长高长大后,母亲就会弯下腰背,往菜苗稠密的地方,拔掉一些柔小枯黄的菜苗。母亲说种菜其实和做人一样,有舍才会有得,哪怕是一棵小小的菜苗也需要适合自己生长的空间、阳光和雨露。
母亲的菜园一直都是用家里的猪粪或木柴火灰来追肥,没有一点化肥农药,每隔一两天母亲就会从家里挑粪水浇一次,让各类蔬菜长得葱茏茂盛。不打农药的菜地,虽然有许多菜叶上常爬有绿色的小青虫,菜叶有窟窿,影响菜的美观,但一点不影响菜品。不像现在的蔬菜,看起来整整索索,那敢直接入口,站在菜摊前都是浓烈的农药味,生食的西红柿黄瓜,回家要多多泡洗,才敢入胃,其它的更要炒熟。
刚进城的那几年,因经济比较困难,每隔一段时间,母亲就让父亲送一大袋自家菜园子的菜到镇上,让妹夫托人带给我,说城里买的菜,农药化肥用的多,日照养分都不足,吃多了人容易生病。那满满一袋子菜,盛满母亲的心血,足够我们吃一个星期。母亲感觉我们的菜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再让父亲为我送新鲜的菜,如此往复,我们夏天基本很少买蔬菜。
如今父亲已不在了,母亲也老了许多,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但她依然固执地在菜园里侍弄。只要有空,就扛起锄头,给菜蔬们除草,给菜蔬们除虫,给菜蔬们施肥。那些菜蔬们也好像是通了灵性似的,西红柿嘟嘟嘟地涨红着脸,茄子紫光照人,还有辣椒黄瓜,也一个个长得油光水滑的,鲜嫩的不得了。这么多新鲜的菜蔬,母亲自然吃不了,她也舍不得买。除了分给我几姐妹外,就送给湾里没有菜园的人家。所以,左邻右舍有什么好吃的,也总忘不了母亲。
现在我每次回去,都会到母亲的菜园里转转,帮母亲除除草、施下肥,看看菜地里硕果累累的情景,每每这时,我总是嘴角流露出得意或自豪的微笑。我知道,虽然离开家乡进城谋生已有十几年了,然而我永远记得自己是虾边庄的一员,永远忘不了自己是农家的儿子。有时我对妻子和孩子们说,等我老了,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哪儿也不去,就回到幕阜山下的虾边庄,接过父母的锄头,继续耕种家里的一亩二分地和母亲的小菜园。妻子有些不屑,说我没出息。可她哪里知道,菜园里有母亲的牵挂,也有我的担忧;菜园里撒满了思念,也结满了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