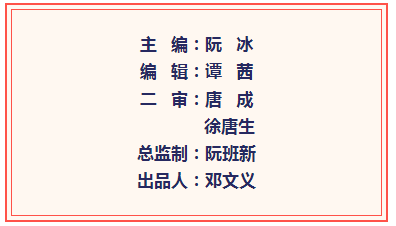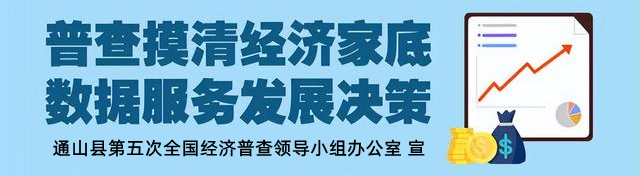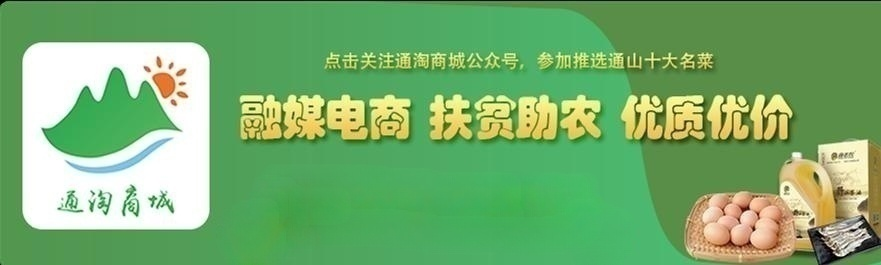风雨“包坨”小桥边
作者:倪霞
那天晚上,女儿提议“到小桥吃包坨”。那是她小时候的记忆,二十多年前偶尔带她吃“宵夜”的地方。这次是女儿和她的令哥哥开车带我和他们的儿子小巴仔。我们三代人,来到“小桥包坨”摊。“小桥包坨”,没有门面,没有门牌,是多年来小城人根据地理环境自发称之为“小桥包坨”,是老通山几代人的记忆。
所谓“小桥包坨”,其实就是老工商银行与老卫生局之间的屋檐下,两个煤炉一口铁锅一个铝锅,两张小桌,架起的夜宵摊子。这个屋檐下的小摊子,风里雨里,承载着小城人的“夜宵生活”一部分。夫妻俩暮色出摊,凌晨收摊,没有城管的追赶,没有白日的繁杂,在深夜的灯光下,在小城进入梦乡之时,在牺牲自己“黑白颠倒”的状态下求生存。
小桥原风景,一直是通山城一道著名的“平民”风景。人来人往,各色小营生在这里尽显人间烟火。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更迭,不变的永远是“小桥流水人家”之风情。我曾经在我的长篇小说《守望木棉花》里,对七十年代末的小桥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小桥一带最深的水域叫仙人潭,岸边柳树成荫,大胆的孩子总是爬上树,然后从树杈上往水里跳。所以,玩水的孩子们为这里取了一个十分调皮搞笑的名字,叫“大卵子”。意为胆大的人有卵子的人才敢跳进水里自由来去。如果碰到胆小不敢跳的人,孩子们会齐声起哄:
么样?冇得卵子吧?跳啊,有卵子就跳啊!
有些孩子之所以能跳下去游起来,还真的是被起哄不服输逼的。这潭仙水,无法阻挡它成为孩子们的戏水天堂……
清楚记得,小桥是1993年重建的。那时候我在妇幼保健院工作,住在老体委,父母住在河对面的卫校,每天上下班或去娘家,必须要过小桥。十多年来小桥坚固如昨。遗憾的是,前几年,大约是2015年,小桥重建,实际上是在原来的小桥旁边突然建了一个建筑物,桥不桥来屋不屋地矗立横陈于水中央,当时旧小桥还没有拆,因为民众和小生意人习惯了旧桥,依然在旧桥上营生和过路。不知是谁,一夜之间突然拆了旧桥,并封堵了原址。市民迫于无奈,只能从现在这处桥非桥的桥上行走。
此桥非彼桥,改了本色失了原味,破坏了原风景;甚至是损坏了曾经一桥新月水中流的风水景观。风水并非“迷信”,观风水即观环境。桥就是桥,桥不是房地产。眼前的“桥”,一个个凌乱不堪的门面关门闭锁于流水之上,大煞风景。如果可以,我想弱弱地问一句,相关部门可否还小桥于旧貌新颜?我相信,将会得到小桥附近居民和所有通山人的鼓与呼。小桥是承载通山人无限记忆的一处小家碧玉似的风景,非常符合通山城的气质。
小桥巷子里的这家包坨小摊,因小桥而名,哪怕没有门牌没有店面,但他是通山人心中的“小桥包坨”。那一对夫妻,在屋檐下在夜色里,寒来暑往几十年,从青春经营,到现在退休年纪,虽然夫妻俩把摊子交给了儿子儿媳,但生活的本质没有改变,它是风雨百姓对生活不屈不挠的坚守,也是小城里底层百姓自力更生的表现。
一天,朋友小聚于老一中,老街夜如白昼,灯火通明。再次路过小桥包坨摊时,只见老摊主正在捏包坨。我问他,今天怎么不是儿子媳妇在这里呢?他说儿子媳妇有事去了,他顶一下。接着我们聊了几句。此处做包坨整整三十年了,他是杨芳林乡人,他做的包坨是正宗的杨芳林水芡包坨,而通山还有一种包坨是蒸熟的芋头和在薯粉里揉成,他的这种,是用开水勾芡再中和到薯粉里揉成。芋头包坨软而糯,水芡坨有筋芡有嚼劲。两种包坨各有秋千,是老一辈通山人过年才能吃的“团团圆圆”,这些都是一代代山里人成长中的记忆,更是现代通山人声名远播、随时可以吃的通山美食。
摊主告诉我,守着包坨摊,日积月累,在新城做起了自建房,孩子也长大了,儿子接承了这份摊业。继续坚守,再次成为又一代通山人的记忆。他还客气地“誇”我:这么多年了,你好像总不老呢,还是那么年轻漂亮。我笑着说谢谢时也誇他,能吃苦还情商高。告别时,两个桌子已经坐了不少人在等着吃包坨。只见一个钢材做的长长窄窄的顶蓬,有四个柱子,柱子下有四个轮子,是可以随时推动的。跟原来的一片塑料布扯起的蓬,有了质的区别,不但方便了,也更能遮风挡雨,这也是时代变迁中的细节。
风雨“包坨”小桥边。他们安静在小城的屋檐下做营生,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勤劳努力,不扰民不添乱,自立更生自食其力。他们是最底层通山人纯朴的代表,让一代代成长起来的通山孩子,以另一种方式记住他们,记住这个城市的一角,记住乡愁的味道。谁又能说,小桥和他们与通山特产“包坨”,不是通山城市建设中的另一道风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