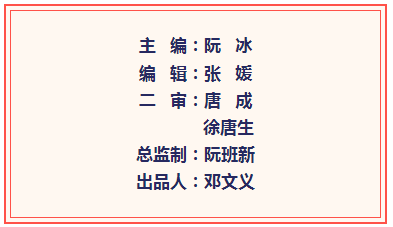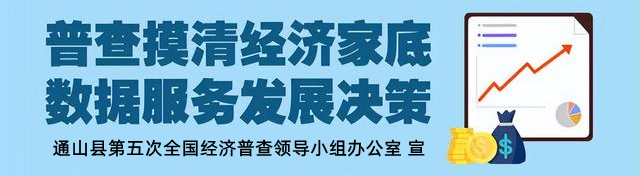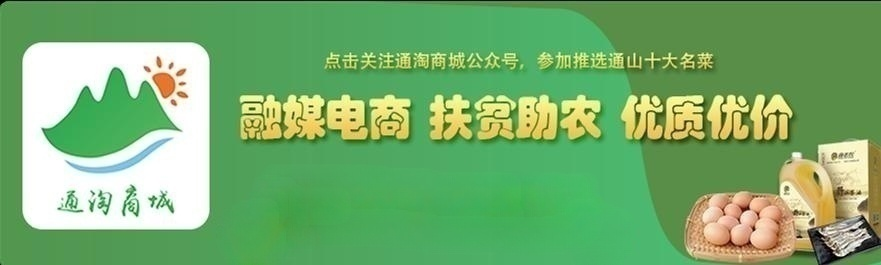老 屋
作者:谢晓文
焦惑典自乔居新街头的新屋后,就鲜少回位于老街的老屋了。
“那年我说卖掉老屋的,老爸硬不让卖。看着老屋,心里就发堵,就要冒火了!”
那年是指焦惑典家搬进新屋的第四年。本来,他可以拆了自己家住的三间老屋耳房重建,没必要另外花五六千元在新街头买屋基建房,就是因为他家的房子,前是老汪家抵着,后是老许家围着,右是老汪家厕所臭着,左是老许家连着,加上两家逐年的扩张,他家的进出,前是被两家相夹的逼仄大门口,后是不到八十厘米的小巷。特别是住了老屋主厢房的老许家,竟然在他家门口,小禾场旁边有一大片菜园。菜园用竹篱笆围着,篱笆每年修整一次。每修整一次,菜园面积就悄悄往外扩展一点。扩展的门前禾场越来越小,他家屋檐的滴水沟越来越窄。随着年龄的增长,焦惑典越住越憋屈,越住越恼火,便产生了另买地基做房子搬离老屋的念头。
老屋是明清时期的两层建筑,高大宽敞,一进三重,青砖到顶,结实牢固。民国时期,开当铺的屋主欠了一屁股债,便以低价出售。焦惑典的祖父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积蓄,一咬牙买下了它。虽然它被放火烧得只剩如今的一重,大门以光秃秃的青石门柱证明烧后的断壁残垣,阁楼门窗精美的雕花在“破四旧”时也被毁得七零八落,呈现残破之貌,但依然可以看见它当年的富丽堂皇。
焦惑典的祖父在他父亲幼年时就去世了。当时,街上一户王家,有点权势,看到焦家孤儿寡母的,便心生不歹之意,使些阴谋欲夺了这老屋,幸亏焦惑典的祖母知书识礼,懂点民国法律知识,凭着一身胆识和聪明才智和王家打官司,最终保住了这老屋。但是解放初,老屋就不全属于焦家了,分给了五家住。另三家很有骨气,经济条件变好后,先后回家乡做了真正属于自己家的房子,搬离了老屋。
从父亲的口中断断续续了解了老屋的历史,焦惑典认为老屋不吉利,易惹麻烦,更加坚定了离开老屋另择地做房子的决心。乔居新房后,他几次动员父母搬到新房住,父亲死活不肯。第四年的一段时间,有人找了他三次,想买老屋。他兴致勃勃地跑去对父亲说:“爸,有人想买老屋,我们赶紧卖了,你和妈搬到出入宽敞的新房住。”
父亲口瞪口呆,说:“老屋怎么能卖呢?它是你祖父用血汗钱买来的,是你祖母用命保住的。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应该把老屋保下去!”
“这样的老屋有什么保头?”焦惑典脱口而出,嗓门大了起来,“被别人家挤占得只剩这小小的一坨了,进进出出得从他们两家房子的夹缝经过,还臭气熏天,亏你住得下去!我看着就恼火!”
父亲固执己见:“不管怎样,老屋就不能卖!必须保!”
“现在好不容易有人买,如果不趁机卖,以后就卖不出去了!”焦惑典一焦急,声如擂鼓。门口李树上的几只麻雀吓得呼啦一声飞跑了。
“卖不出去更好!我在,老屋在!”父系犟得像头牛。焦惑典和父亲闹得不欢而散后,一年回不了老屋两三次。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焦惑典的父母相继去世。这一天,虽然中午时分下过一阵雨,但是地面还是腾腾地冒着热气,撩拨着人们的烦躁。下午四点钟,焦惑典骑着摩托车,带着两大蛇皮袋的包袱,大汗㵉漓地出现在老屋大门口——中元节,他必须带着家人来到老屋堂前给祖宗和先父先母烧火纸,送冥币。
大门口似乎更狭窄了,深深地凹了进去——两边的老许家和老汪家,几年前把下堂屋的房子重新翻建成了三层楼房,借机往老街面和老屋大门口扩展了一点面积,而他家位于中左部的房子成了死角,像只锁在小笼子的困兽动弹不得。焦惑典停好摩托车,放下蛇皮袋,黑着脸看着眼前似风烛残年般摇摇欲坠的自家房子,胸中的火又腾腾地冒上来,心里只想爆粗口,大骂个痛快。
想归想,胆小怕事的他做不出公然骂街的行为。他依然和往年中元节一样,憋着一肚子火,扛着两袋火纸跨过青石门槛,迈过青石天井,上到高大宽敞的堂前。堂前的泥巴地面早已坑坑洼洼,极不平整。他起过无数次要将堂前地面打成水泥地面的念头,都因牵涉到隔壁老许家,只好作罢。但是,即使是这样坑坑洼洼的地面,也被老许家放了许多东西,靠他家的这边竟然还被安置了一个割扳机,往年烧火纸的地方也堆了一些工具——这是赤裸裸的霸占啊!有心脏病的他气得发起抖来。妻子看到他这样,担心地拉了一下他的手,说:“我去找他们说,叫他们退出来。”焦惑典性格内向,在外不善言辞。妻子则相反,找人理论的事大多是妻子出面。
一会儿,妻子和老许家那个听说年轻时学过几下武功的上门女婿小柴一前一后地过来了。小柴麻利地收拾出一块空地,转身就走。焦惑典在小柴转身那一刻,突然蹦出一句话:“这堂前东西你们退干净,我们自己要用。”小柴扭过身来冷冷地说:“你们不在这住,哪用得着?”“即使我们不用,你们要用,也应该上门打声招呼,经得我家同意。”妻子说。
“用自己家的堂前还用得着和你们说吗?”小柴睨着眼,一副随时准备上的架势。
“堂前怎么就成了你们家的?”焦惑典脸色铁青,浑身抖得更厉害了。
“我们在这住了几十年,堂前当然有我们的一半。”
“你……”焦惑典只觉得一口血涌了上头,堵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他捂住胸口,扶着墙壁,大口喘着气。妻子见状,忙走过去扶着他,轻轻抚摸他的胸口。
半小时后,焦惑典的子女们赶到了现场,帮忙堆好包袱。袱烧完后,一家人离开了让他们倍感压抑和愤懑的老屋。
回到家的焦惑典,缓过气来,又像往常一样冲着妻子发泄着内心的愤怒。
妻子压低声音劝阻:“你声音也放小点,隔壁邻舍都听着呢。”
他声音愈发大了:“我怕啥?老屋本来就是我们家的!老许老汪他们两家不要脸!解放初,政府看他们没房住,就分一两间房子给他们住。他们住了几十年,不想退,这倒罢了,现在竟然想霸占堂前。”
妻子摇摇头,小声嘀咕:“老是这话!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有本事,你到外面逞强去,把被他们占用的房子要回来!”
历史原因,要回房子是不可能的,但堂屋绝不能让他们占了去!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焦惑典前往县城向一个律师咨询。
“有房产证吗?有房屋买卖契约吗?”律师问。
“民国时买的房不知道有没有房产证,但我爷爷买房的时候肯定是有买房契约的。可是我祖父和祖母去世得早。他们去世时,我父亲只有7岁和12岁呢,而且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等许多政治运动,买房契约可能早弄丢了或者被毁了。”焦惑典摸了摸头,沮丧地说。
“没有证据证明这老屋是你们焦家的,那么你向法院提起诉讼,是胜诉不了的。”
“可是茶香街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知道这老屋是我祖父买的,知道我祖父的姓名叫焦大成——姓焦呢?老屋姓焦呢?是焦家的!而隔壁家姓许呢。而且,当年房子不是土改给他们的,他们没有土改证的。”焦惑典急了,语无伦次。
“这样吧,你先回去找一找买房契约,找一找街上的老人家证实。如果房子确实是你祖父买的,请他们帮忙写证词,能出庭作证更好。证据准备充足后,我再帮你写起诉书,提交法院。”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焦惑典吁了一口气,抬头看看天空,一缕阳光正从乌云中透射出来,刺得他眯起了眼。他马不停蹄地赶回乡下,接连两三天,和妻子两人上了两三家老人的门,陪着笑脸请他们说实话证明实情。他这次下定决心要用法律维权,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他相信司法是公正的,司法会帮助他保住堂屋!
出庭这一天,焦惑典特意穿上新买的中山服,头发抹上儿子的摩丝,梳得光溜溜的。陈述时,往日不善言辞的他竟口若悬河,不带半点梗阻;出具两份证人证词,请躬身驼背、拄着拐杖走路的姜老大娘出来作证时,他更是声若洪钟,中气十足。可是当老许家拿出土改时期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时,他傻眼了,感觉一根根头发竖了起来,随即声嘶力竭地喊:“这土改证这么新,肯定是假的!是假的!”
“肃静!肃静!”法官敲了敲桌子,说,“是真是假,法院自会拿去鉴定。”
在法庭调查阶段,焦惑典茶饭不思,坐卧不安,那张繁体字的房产证就像条毒蛇一样,日夜盘踞在他心头。他身形日渐消瘦,有人甚至怀疑他得了癌症,委婉地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他自己和妻子深知个中原因,自然不予理会。
好不容易熬来了法庭辩论。这一天艳阳高照,清风阵阵袭来,吹得人心里甚是舒坦。焦惑典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似的,忐忑不安地随同诉讼代理人坐在法庭中,直到老许家的小柴主动承认房产证是他自己伪造的,他的心才落到实处。法院工作人员在调查阶段向老许家普及了一些法律知识。老许家的上门女婿小柴知道了出示伪证,会被罚款、拘留,严重的话,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便主动向工作人员承认了房产证是假的,是他在看到一个专做证件的广告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向对方打电话询问,对方说可以,他便破釜沉舟花800元买了这个假的房产证。
法院判决书出来那天晚上,焦惑典特意嘱咐妻子做几个好菜,拿出十年前女婿提来的,他一直珍藏着的两瓶茅台酒,邀上三个至亲好友,喝得个酩酊大醉。
后来,茶香街的人看到他越活越有精神,身形渐渐发了福,曾经蜡黄的脸也白里透红了。他经常站在门口翻阅一本鲜红封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见得多的人便打趣他了:“老焦,你这是要去当律师啊。”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闲暇时了解一下法律知识好。当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就知道怎样维护我们的权益。”
有人故意泼他的冷水:“打官司还不是要讲关系?谁背景好、关系多,谁就会赢得官司。”
“错!”焦惑典就正色道,“我国的司法是很公正的。我家情况你知道吧?没关系,没门路,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老屋堂前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属于我家。但考虑到老许家没堂屋,可允许他家在我家老屋堂前做红白喜事。”
但焦惑典一直没对人说,老许家的那个小柴,因为主动坦白,认错态度好,并没有因为出示伪证被拘留,而只是被罚款三千元。
作者简介:谢晓文,一个在文字里谋心、栖心、修心的随性女子,一个淡名寡利、率直耿正的痴傻儿,红尘里嬉笑,杏坛上较真,现任职于湖北省通山县实验中学,湖北省咸宁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