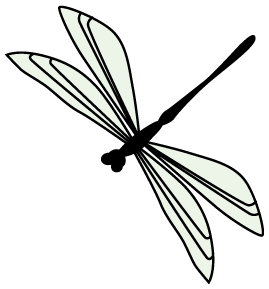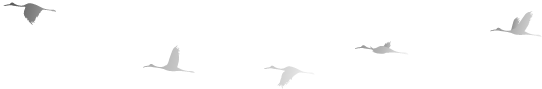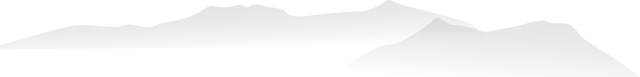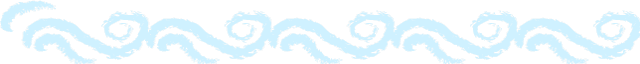六月中旬的一个日子,我爬上了幕阜山脉中段、海拔400米的鸡口山,走在一条看似很寻常的山路上。这其实是座英雄的山脉,一条红色的山路。鸡口山自古就是军事要塞,无法估算有多少革命志士在这条山路上往来,也无法估算这条山路上洒下了多少的汗水和鲜血。今人之所以称这条山路为古道,是因为连接大畈与黄沙的交通要道,在山腰的险要处,一道石门将山路分成两段:一段可遥望浩渺的富水湖,另一段一直通往黄沙铺镇的阮家墩。这条山路又被叫作是红军路,那是因为阮旦明、叶金波、谭俊华等人在这里播下了红色的种子,那是因为开国元勋王平、阮贤榜等将军从这里开启长征之路。
这是我第二次翻越这座山、走这条路了。三年前的暮春,第一次面对这座山。对于一个在山区长大的人,对山总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甚至是敬仰。但鸡口山不高大,也不神秘,普通的像故乡山野里的一朵花儿。那时踏上它的领域,不过是一种户外踏青的体验,心里似乎没有更多的虔诚。那一次我登上鸡口山的山脊,看那高远的蓝天下,重重叠叠、层层而去的山影,也会久久地如痴如醉地眺望着,遐想着。时至今日,想起那种空灵凄幽的山影,依然禁不住心神摇动。那份宁谧、那份幽远的韵致,真让人如啜饮清泉,一下涤净了心头的尘俗。古往今来,人们游历山川,除了欣赏大自然的秀美风光,不外乎获取履艰越险的快慰之感,我以为,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心灵与静美的山水相洽相融,排遣胸中的郁结。 但这一次,是山路的牵引,还是山影的感召,抑或是性灵的醒悟?让我如此渴望沿着这条山路走近这座山。
晌午,阳光炽烈地照着阮家墩背后的山坡上。这个时节,薄薄地生长着一层茅草的山坡上,一堆又一堆山石分布在倾斜的山坡上,土壤的浅黄色从枝叶里露出来,竟然也会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灼人的亮光来。群山由北向南,沿着流云的足迹,形成了一道陡坎,它的西南是山的阵营,东面便是一片宽阔的平川,再往东,还是一片山。因此,云朵在天空里的漂泊,根本不会在意从高天上望下来的这一道皱褶,不会在意陡坎下面蓝荧荧的一片水域,更不会在意水域侧畔紧贴着山脚的一个村庄。然而这个村庄确实是存在的,阳光照耀着层层叠叠的群山的时候,同样也一视同仁地照耀着山脚下那个叫做阮家墩的村庄。
虽然它有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称:阮家墩,在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一场短暂的春雨就可以把它严严实实地遮盖,一些庄稼也会把它染绿,并且混在众多的植物里。就这样,这个叫做阮家墩的村庄,无论是从古到今,还是从内到外,都没有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来。直到某一天,这个村庄,跟某些人,以某种关系联系在一起,人们才开始慢慢地去关注它,靠近它,审视它,并且慢慢地相信,这个村庄,其实是一粒种子、一颗果实,当它在历史泥土里埋藏了太长的时光,在群山巨大的影子里独自发芽、生根,迎风生长,一直没有谁给予过它足够的关注。当它开出了一朵硕大而鲜艳的花朵,那奔放而热烈的色彩用灼目的光芒把阳光都反射回去,人们才发现,这个村庄自始至终,都极不寻常。
历史就像是一潭深水,扎个猛子下去,可以抵达某个深度。在鄂南的山山水水,有着许许多多的革命印记。关于阮家墩这个村庄,历史的记忆重新返回到1926年。许多人,许多次谈到这个历史故事,这个故事既是黄沙铺的,也是阮家墩的。阮家墩是到黄沙铺的第一站,所以阮家墩是幸运的,也是英雄的。阮旦明、叶金波一定从这条山路走过,何长工、李灿率领红五纵队一定从这里走过,鄂东南特委书记吴致民会见何长工走过这里,在黄沙铺召开的鄂东南14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代表走过这里,鄂东南道委机关、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中共河北特委等机关的革命志士走过这里。那时的黄沙铺成为鄂东南苏维埃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期间,黄沙地区就有5000余名热血青年参加红军,他们中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阮耕、全忠、宋立昌、叶发全、阮旦明、潘际汉等。有的成为开国将领和党的领导干部,王平、贺俊贞、阮贤榜、梅盛伟、王权堂、阮汉清、阮帮和、赵敏涌等就是从这块热土上走出去的。
人在大地上的行走,旅程上的许多驿站,有些是无法磨灭的。比如,阮旦明从这条山路出发,一直到他抵达革命道路的这一段距离。当历史缓缓地掩上它那些覆尘的纸页,记忆也就开始了。尽管谁也无法去还原他曾经在那一段漫长的山水之间艰难行走的情形。然而,当他从这条山路抵达阮家墩的时候,这个地方便会成为他生命里极深极深的一个刻度。比如,阮旦明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把自己的身影陈放在这段山路,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晨昏,并且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在数年以后,我们通过回望历史,才发现,他已经把这个地方当成了他生命里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一个人的生命流向,在很多时候跟一条大河的流向极其相似。阮旦明在黄沙铺的这个起点,同样也呈现出了相同的特征。百年前,阮旦明通过从鸡口山的这条路,沿着富水河逆流而上或顺水而下,播洒热血和革命精神。黄沙铺以及富水河流域的人们,肯定有人无数次抬起头来,看见神秘而高远的天空,天上的云朵渐渐变红变亮。躬耕之外,阮旦明应是以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往来于通山和黄沙铺之间。这一段时光,他是从黄沙铺射向鄂南大地的箭群中纤细而锋利的一枝,狼烟燃起,阮旦明顺着革命的长缨所指,日奔夜袭,烟尘覆面,霜凝须眉,当他踏马远去,在他贴身的衣袋里,始终存放着一把金钥匙,让他随时都可以在某个时刻打开自己。在这里,生活的气息隐藏了盾牌的坚不可摧,硝烟渐散后,许多村里人还会看到那些远去的兵士们耳廓后面淡淡的血痕。在这片狭窄的土地上,一些生命在箭簇与刀光中枯萎,深红色的血迹风干之后,在脆弱的宣纸上,功勋显现出来,从这条山路上走出来,成为村庄里的景物和故事。

站在山腰凉亭上眺望,阮家墩西面的山坡上是一片接一片的庄稼地,东面也是一片接一片的庄稼地。庄稼地里生长着水稻、玉米、茄子、辣椒、番茄、花生、黄瓜……这些植物以水分、阳光、有机肥作为纽带,填满了村里人的每一段匆忙的时刻,让他们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去关注,让他们的脸庞一回又一回地去贴近,让他们的心跳一声又一声地去回应,植物在它们的生命轮回里一岁一枯荣,村里人则在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地把新的生命从村子里牵出来,让一个家族执著地穿越深远的时光隧道,去接受每一轮阳光温暖地照到他们的额头上,从不迟到。为了在村庄外面与庄稼们的成熟相遇,村里人在清晨早起,裤脚拂过石阶上的荒草,踏着野畴里草尖上的露珠,绕开树篱附近在晨雾里漂飞的夜萤,开始守候水流潺潺淌进田地里,潜入密密麻麻的根须。流水源于大幕山上那些密林,浓荫覆盖着倾斜的山坡,水分滋生,它们潜藏在泥土里,被坡上的密林严严实实地围裹着。林子中间,往往会有一片深绿色的草地,星星点点的野花旁边,零散地生长着野菌子、野浆果、野鸟的空巢。在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晨昏,流水就是从半坡上的密林里淌出来的。它们出了林间,渗进低洼处,便形成了静脉一样纤柔的细流,像一个乖巧的小女孩清晨上学一样,蹦蹦跳跳地向着山下红红绿绿的庄稼地里奔去。当它们在田畴里左冲右突地穿行,常常会听见植物们的根茎发出此起彼伏地拔节的声响,雨打轩窗一样,与水声交织在一起。这时候,人们就会发现,村庄外面的田野里,到处都是诞生的生命。而这些生命居住在植物们绿色的汁液里,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村庄里人们的呼吸一起深情地互相唱和。
当历史的漫长让人们渐渐失去记忆时,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重新又看到了过往,检视今天,让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在南鄂的大地上发出久久回荡的声音。于是,我们用方言去慰藉方言,用信念去验证信念,用目光去温暖目光。黄沙铺在这个时候,又有了不仅仅只属于他们的红色土地,大幕山的天空,漂荡的星星一粒一粒地亮了起来。
编后语:通山广播电视台APP云上通山“文化”栏目的文学作品投稿邮箱:365278228@qq.com,方雷收,附与文字有关的图片6张,个人简介及个人图片。部分作品还可刊登通山政务网,通山周刊。期盼惠寄更多的佳作,让父老乡亲分享您的写作快乐感。谢谢!
郑安国,笔名:隐水郑歌、郑歌,1976年出生,通山隐水人。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湖北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新快报等发表散文、诗歌、小说、评论、新闻等作品近100万字。现任《咸宁周刊》副社长、《九头鸟》执行主编、《通山文艺》执行主编。咸宁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咸宁市评论家协会理事、咸宁市小说家学会副会长、通山县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通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
长按识别二维码
下载云上通山
作 者| 郑安国
编 辑 |徐 微
编 审 | 唐尚伟
监 制 | 方 雷
总监制 | 阮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