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突然要我们兄弟姐妹们都回来,个个慌死了往家里跑,都以为母亲病了。见到母亲好好的,心想:不是年不是节的,叫我们都回来干吗?
母亲在餐桌上笑着说:“有件事跟你们说,单位通知要办社保,每个人交三万块钱,你们说交吗?”
一听是这事,兄弟姐妹们各自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九九。
从市里赶回的三弟说:“这事啊?好事啊,交呗,不就是三万块钱。”
小妹往母亲的碗里夹了块肉,说:“好事是好事,妈呀,您这大年纪了,还交这钱干吗?三万说不多也不少呢,再说,每月才领三百多块钱,什么时候捞回本啊。”
小妹怕又要摊钱,她目前经济比较困难,两个小孩正上大学,月月要钱用。老大平常不爱多说话,他赞同小妹的意见,他说:“就是嘛,能领多长时间呢?我有个邻居,上个月刚交了养老保险,前天得急病死了,人家只赔了几千块钱的安葬费,划不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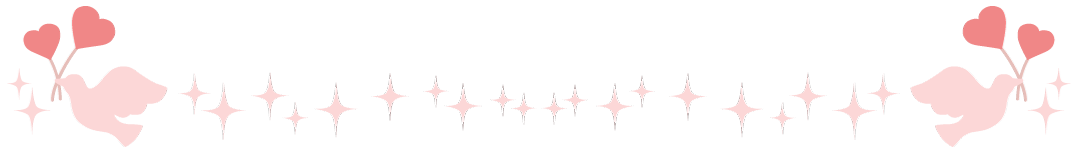

母亲一听就不笑了,只顾往嘴里扒饭。看见母亲那失望的样子,桌上就冷了场。父亲说:“你们再商量商量吧,不是什么大事,这多年不也过来了?”
母亲原先是有单位的,后来县级所有国企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母亲那单位破产了,单位没钱交社保,每人只发了几千块钱。单位破产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自己觉得像是没了娘的孩子,(这使我想起大革命时期失去组织的红军)很不开心,很少出去玩,更不愿跟别人说自己的单位破产的事,总觉得矮人一等似的,一旦别人说起这类的事,母亲不是叉开话题,就是自己走开。母亲全靠父亲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两个老人用不了多少钱,不靠社保日子也过得去。
吃过饭后,小妹说家里有事要赶回去,临走时说:“你们定吧,要交就交,可我现在没钱。”
老大电话不停,都是催他上桌打麻将的,没表态就走了。老三下午市里有个会,他对父母说:“交吧,他们没钱我出,等他们有钱了再还给我,哈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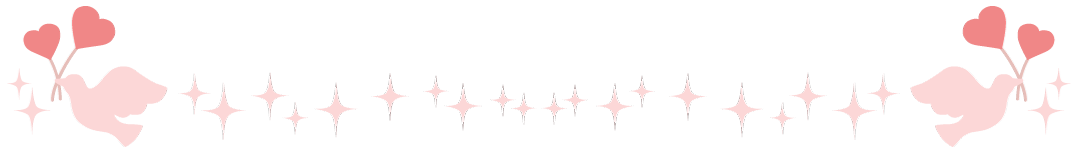

他们一走,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洗完碗筷,收拾好桌子,想陪俩老坐坐,父亲说:“二妞,你也回吧,你比他们都忙,也困难。”
“那行,您们定好了就叫我,我帮妈去办。”
其实,我打内心也想不通,也不赞成母亲交社保,钱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年纪大了,是小妹说的还能领几年呢?
有好几天没听到父母的消息,我以为他们放弃了,打电话一问,母亲的社保费交了,父亲说不交咋办,打那天开始你妈就闹病,像小孩似的不吃不喝,闹得心烦。我忙问现在呢?父亲说早好了,高兴着呢,整天跟老太婆们又说又笑的打纸牌。
想想父亲说母亲像小孩的话,我笑了,真是老话说的,老如小。
这日子还真像水,舒心的,操心的,富裕的,贫困的,都是过坎过沟的往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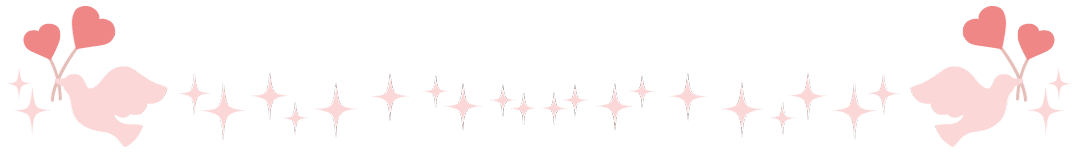

年底,母亲真的病了,哮喘病又发了,每年都这样,天气一冷,哮喘病就复发。几个电话,兄弟姐妹们都回来了,父母的屋里又乱糟糟的像我的店铺。
小妹还没进屋就哭着喊妈,进到妈床前就泣不成声了,妈说:“臭丫头,哭啥?我还没死呢,我死不了的。”
母亲这次好像比去年严重些,当着母亲的面不好说,我们兄弟姐妹们背着母亲商量后事的事,什么遗像,什么寿衣,什么墓地的都得提前准备好。一些亲戚也闻讯赶来,似乎是最后的见面。倒是母亲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见到远地亲戚格外高兴,拉着手咳咳喘喘地问七问八说个不停。
乡下的舅舅对妈说:“老妹哎,现在农村可好了,种田国家还给钱,我每个月还有几十块钱的养老费呢,吃喝不愁。”
母亲说:“那好啊,那我就放心了,我每月也领工资,多是不多,够用,听说明年又要加。老哥啊,好好活着吧。”
母亲说这话时完全不是病人,一脸的笑,声音比以前要大好些,很自豪的样子。(图:来源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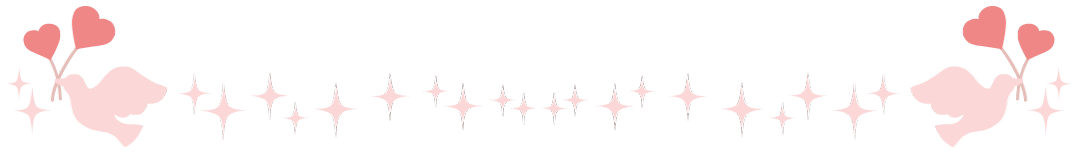

作者简介:阿木,原名王运木,通山县文学艺术联合会退休干部,咸宁市小说学会名誉会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在《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当代作家》《小说界》《小说月刊》《青年作家》《中国文学》等几十家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已出版微型小说集《没有故事的女人》《蝉歌》《难说的事》、中篇小说集《戏台》、长篇小说《梅殇》。
长篇小说《梅殇》获首届“浩然文学奖”,中篇小说《海棠花开》获《中华文学》杂志2018年度优秀小说奖,短篇小说《县长钓鱼》获《水利报》、中国作协创联部联合举办的“河长杯”全国征文二等奖,微型小说《阳台的故事》获湖北省第二届微型小说大赛铜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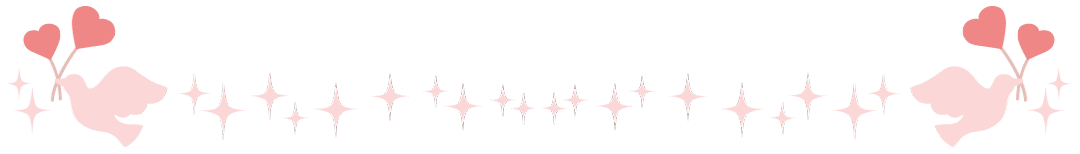

主 编:阮 冰
编 辑:谭 茜
编 审:唐尚伟
监 制:方 雷
总监制:阮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