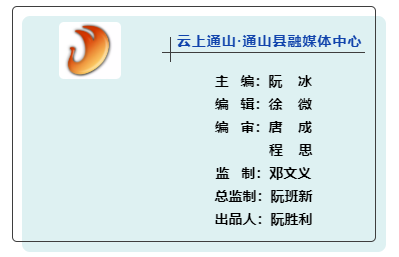“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不知道这是第几场秋雨了,只看到院角的柿子树上,几个红彤彤的柿子矗立枝头,孤独的在寒风中摇摆。
气温跌到老低老低,坐在阳台上,阵阵凉意从脚后跟渗到全身,冷噤一串接着一串,该换棉拖了。
壁柜里整整齐齐码着不少棉拖,有后跟的、无后跟的,高帮的、矮帮的,大码的、小码的,足有二十几双。虽然模样并不好看,但做工还算精细,鞋面也柔软厚实。
棉拖放了好多年,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穿,每年拿出来洗洗灰尘,晒晒潮气,便又小心的用袋子装好,收进橱柜。每次收捡棉拖,母亲那佝偻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

那年立冬,先后动过两次手术,腕骨和股骨粉粹性骨折的母亲,刚刚痊愈。虽说是痊愈,但毕竟80岁了,经几次折腾,腿脚无法完全恢复,行动还是不便。我与妻子晨练回家,母亲不在家,楼上楼下的邻居也不曾见过母亲,不喜欢出门的她,会去哪呢?
时间每分每秒都在煎熬着我,两小时快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音讯。我骑上电动车,沿着街道疯跑,脑海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去寻找。亲戚电话打了一个遍,没有一点消息,周边店铺问了一个圈,也没人见有意外发生,我迷茫了,六神无主了,惊悚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近中午时分,远远的看到前面一位老人,佝偻着腰,跨着一个帆布包,步履蹒跚地向前缓慢挪动。是她,是母亲。看到她的背影,看到她佝偻的、两脚高低不平的背影,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没有多说,把背包绑在后备箱上,将母亲扶上电动车,叮嘱她坐稳、坐好、抓紧,母亲双手环抱着我的腰,很紧很紧,我明显感觉到了她的紧张,估计是看到我一脸的严肃吧。
车子动了,母亲抱得更紧,似乎怕我马上会离她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
回到家,母亲告诉我,天冷了,她就是想去街上买点鞋底和面布,在有生之年为我们兄弟姊妹做几双棉拖。责怪的言语瞬时被击碎,我睁大眼睛,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母亲从小失去父亲,是外婆一人拉扯大,只读了三年书,识字不多,但母亲从小聪慧,年轻时裁衣、纳鞋、绣花,样样“精通”,特别是在鞋垫上画花,拿笔就来,从不需要“打草稿”,画的荷花、梅花和菊花都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沉默了几分钟,妻子打破了令人窒息的宁静,轻声说,人生地不熟的,腿脚又不方便,万一出个意外,那可咋整哟?
母亲低着头,像小孩子做错了事一样,颤抖地说,以后不会了,不会了。望着满头银发的老母亲,我还能有什么理由再责怪于她?

后来,母亲真的就很少走出房门,总是待在家中,带着老花镜,用她那布满老茧的手,盘弄着她的棉拖。
母亲年纪大了,双眼不再明亮,身姿不再挺拔,双手也不再灵巧,她是缝了又拆,拆了又缝,也不知道反反复复了多少次,每次喊我穿针,我都说,算了吧,买几双算了。母亲望着我笑笑,不予理会。
棉拖完工了,母亲一身的轻松,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将棉拖一双双摆在阳台上,守护着它们,就像当初守护着她的六个儿女。这几双是给老大的,这几双是给老二的,这边的是给老三的,这边的是给老四的,老五家人多,要多给两双,剩下的给老幺。她这样分分,那样分分,搬过来,倒过去,忙活了好几天。
我告诉她,这么多的棉拖,穿不完的。她笑答,现在还爬得动,多做几双,哪天看不见了,爬不动了,就不能替你们做了。
大前年元旦,母亲因病撒手人寰。院角的柿子树下再也不见母亲的身影,她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的一群儿女。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牵挂和她亲手缝制的一双又一双棉拖。
带着母亲余温的一双双棉拖,像一条条小船,载着儿子的牵挂,飘向远方……
夜已深,窗外,寒风凛冽,窗内,穿着母亲做的棉拖,不会再冷。
作者简介
程浩,湖北通山人,任职于通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作协会员,因工作需要与文字结缘,写实在的文字,做实在的人是终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