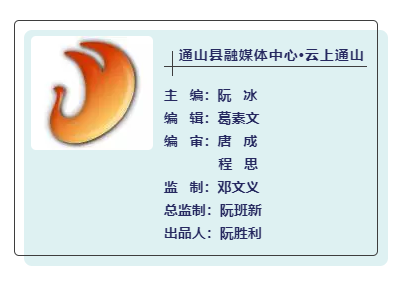忆祖母
作者:袁丽明

一场突如其来的雨,阻隔了四月的春光与暖意。我数着窗外那些胡乱蹦跳的雨滴,它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就别离了云层,在瓦片上,在水坑里,在大地每一寸裸露的肌肤中,它们落地的时候都会倔强地回弹,溅起一朵清晰的水花,似乎在回望自己曾经是一朵云的模样。我捋着同样胡乱的心情,在送走祖母的这个雨天里,回忆着与祖母有关的点点滴滴。
大概要从12年前说起吧,那时候我刚成家。成家前我曾幻想过憧憬过未来新家的模样,若是夫家能有爷爷奶奶,那该多好。我喜欢与老人家相处,喜欢听他们讲述曾经的故事,每一个老人都有丰厚的阅历和见识,每一个老人都是一部独特的书,深邃厚重,有光芒照亮我们前行,有能量滋养我们成长,有内涵丰盈我们的心灵。从小我就是听着奶奶的故事长大的,可惜奶奶走得早。幸运的是,我如愿以偿,夫家里,有待我如宝的爷爷奶奶。

我们家与祖母家大概相隔一百米。平时,我们有新的住所,很少回来。为数不多的居家日子,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祖母家围着两位老人转悠。火炉旁,菜园边,禾场磡;烤火,种菜,劈柴……我们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两位老人的脸上,始终有着花一般的笑容,慈祥可亲。在初来乍到的新家里,感受不到丝毫的不安,倒像我生来就是这家的一份子,只是阔别多日再归来。
那时刚过古稀之年的祖母,虽然步履蹒跚,可身体还是很健康的,她做农活很干练,在村里不输于一个年轻的劳动力。祖母家地里种着,圈里养着,蔬菜瓜果满架,鸡鸭猪狗哼嗷,她一天到晚进进出出过得跟年轻时一样忙碌。长竹笋的季节,正好也是耕稼的旺季,每天鸡豚哼着歌谣各自回窝的时候,就能见她夹着农具从外面归来,先清点鸡豚,后准备晚饭。有时候掐一把葱的功夫,她用眼眸的余光扫了一下还未黑尽的四野,放下葱苗,拍拍围兜,便挎着竹篮钻进山林了。从夜幕降临到伸手不见五指,眨眼功夫,祖母就扛着竹笋回来了。用村人的话说,那钻林的劲头就如猛虎一般。

我们都感叹祖母,一把年纪了还在奔波劳碌,该享福了。祖母却不认输般认为,自己还能做。她常说年轻时的故事,总觉得与年轻时相比,现在差得太远了。祖母有六个孩子,每一个孩子从怀到生,她都是不分日夜在劳作。白天随着生产队的劳动力在队里出工,晚上在家里浆衣洗裳缝缝补补,一直干到孩子出生那一刻。祖母常说她生姑姑的时候,正逢打薯粉。薯粉工艺复杂,过程也很漫长。把红薯洗净、磨碎、过滤,静置,倒水,晒干。那天祖母一直在洗薯,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大大小小的水缸啊木桶啊摆满了禾场,架子上的滤网在祖母手中左右摇晃,吱吱呀呀。磨好的薯,滤好的粉,一字排开。祖母一会低头弯腰在桶里舀薯,一会挺直腰杆掌着滤网在摇粉,白花花的浆水滤出来满了缸、满了桶。白天从早到晚,没顾上松口气,晚上姑姑就出生了。祖母的一辈子,是忙碌的一辈子,也是要强的一辈子,她的筋骨如钢筋水泥浇灌的一样,不知道苦,不知道累;她像一颗陀螺,在生活的鞭子下,始终保持充足的能量,始终不停地、热烈地转……
祖母最会做包子了。不忙的时候,她会搬出家里最大号不锈钢盆,洗净不常用的最大号锅,揉粉,炒馅,架火,叮叮当当,把厨房整得烟熏火燎的,这是她要给孩子们蒸包子了。做好的包子用袋子装好,一袋一袋的,儿的、女的、孙的,身边的,县城的,只要能送到的,都有份。家里种的蔬菜瓜果熟了,老母鸡下蛋了,祖母也会迈着蹒跚的步伐送到各孩子家。每次孩子们回家看望,祖母更是想方设法给孩子们做吃的,煮坨、煮鸡蛋、找零食,她的家像个百宝箱,总是储备着这些,随时都能拿出。要说她晚年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还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尽管家人们百般阻挠,不准她种庄稼了,她还是偷偷种。天下父母心大概都是如此,不管自己多大年龄,尽管孩子早已长大,总是想着给予,总是想着付出,只要自己还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就会很快乐。至少,祖母是这样的。
我们总说家有老是个宝,娘家祖母去世后,时隔5年来到夫家,重新拥有敬爱的祖父祖母,我百般珍惜我曾拥有至宝的时光。可是,岁月不饶人呐!尽管祖母在我们心中如钢铁一般坚硬,可是在岁月车轮的碾压下,她还是不得不服老,不得不认输。
80岁以后的祖母,身体每况愈下,只是她那不服输的倔强丝毫没减。每次从医院出来,元气稍一恢复,她就不听劝阻开始忙碌。不管孩子们怎么挽留,她都要回自己家里过夜,那些鸡啊菜啊,都是她的宝贝疙瘩,为了它们,祖母说什么都要回家。如今想来,那些家伙身上都是承载着祖母的厚望与欢喜,因为她们可以满足祖母给孩子送东西的全部愿望。直到因为中风倒地,生活无法自理,她才不得不接受现实,跟孩子们住一起。

今年过完年,祖母的状态就不怎么好了,以前可以毫不费力喂她吃完一碗饭。年后,她的嘴巴像一扇老旧的房门,喂一口,嘴巴合拢咀嚼许久,听到喉间咕咚一声细响,再才慢悠悠松开牙床接第二口。每一次张开与闭合都十分缓慢,一次也吃不了几口,就再也不肯打开了。祖母与人世间的情缘,也像这不肯张开的牙床一样,渐渐关闭,渐渐封锁。家人守着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神色一点点暗淡,一点点消逝。在她生命最后半个月里,我几乎天天下班后就直奔家里,看一眼祖母,然后再于夜深时驱车返回,半小时的车途,我一新手司机,有时路过黑漆漆的七里冲时,会有一丝怕意,但每次都能很幸运的遇到过往车辆,突然就不怕了。
祖母如一盏灯火,熬至油尽灯枯,在她83岁那年,一个春末,她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12年的祖孙情缘,不是一纸可以写完的;12个春秋里,有太多的回忆在脑门回旋。
从此,我再没有祖母了……